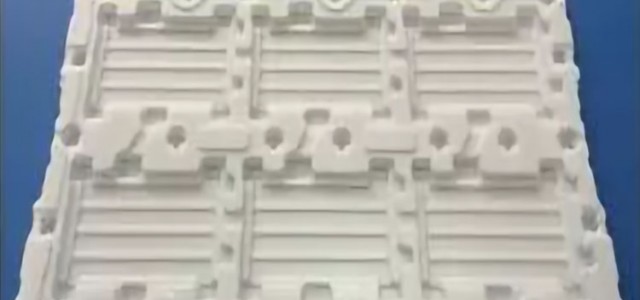12月30日電 據馬來西亞《星洲日報》報道,在馬來西亞的小鎮街場或老城區,少不了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傳統中藥店。從上個世紀到這個世紀,不少中藥行慢慢從人們的視線消失,但由劉氏一家人堅守近80年的葆和堂,至今仍屹立在柔佛州居鑾毛申律大街上,守護家傳中醫藥業門楣。
“我的父親特別交代,我們家必須堅持傳統的中醫、中藥,不可轉型去賣奶粉、尿片之類的雜貨,將葆和堂變成像是迷你市場一般。”葆和堂店主劉凱說。
中藥業非夕陽行業
葆和堂目前由第四代子孫劉凱當家。他提到,雖然許多中藥行抵不住時代的洪流,逐漸式微,但他并不認為中醫藥業是夕陽行業。身為中藥師的他指出,現代人的健康意識普遍提高,會盡量減少服用或對人體產生副作用的西藥,轉而選用滋補養生、調理體質的中藥。
“現在的網絡發達,只需在網上搜尋資料,就可增加對藥材的認識。中醫藥的學問很多,越是深入鉆研,就越是贊嘆古人的智慧。經過多年厚積薄發,現在也有不少友族愿意嘗試中藥,令中醫藥業另有市場。”
劉凱提到,中醫師和中藥師就如西醫體系中的醫生和藥劑師,但中藥講求的是對癥下藥,就連咳嗽、傷風等小病,都要識別類型施藥,如熱咳、寒咳、過敏、風寒、暑濕等,在用藥時都大有不同,調養身體的藥方更是多不勝數,需具備專業的知識及判斷。
他14歲的女兒劉筱彤自小就對中醫藥業感興趣,常到葆和堂里下打手,只要是放假期間,都會在店里協助運作及學習,有望將葆和堂繼承下去,成為第五代的接班人。
藥材講求貨真價實
“葆和堂并不是自詡老字號,而是一代一代的傳承,依循祖訓‘童叟無欺’,所以我們除了積累經驗,也對店內售賣的藥材非常講究,全都貨真價實,也因此令消費者充滿信心。”
劉凱也提到,中藥行的日常工作繁瑣,做過中藥業,就不懼其他行業的艱辛。“我們的日常就是要處理藥材,藥材送到后,需經過處理才能販售,而藥材的種類那么多,每一種的處理方式都不一樣,有的要日曬,有的需陰涼,非常瑣碎。若處理不當,藥材有可能生蛀蟲。”
以往藥材的價格上上下下,很不穩定,現在因貨源吃緊,價格只上不下,也令中醫藥業面對難題。“中藥材的貨源難找,本地因氣候、土壤的關系,出產的藥材品質不如中國進口的,但早期中國藥材還有大量出口,如今越來越多人選服中藥,中國內銷市場龐大,出口到國外的數量就減少了。”
此外,為病患煎藥也是葆和堂的服務之一,要很有耐心地看顧煎藥的火候。“以往也曾嘗試過以方便的電子藥煲來煎藥,但效果不理想,所以我們還是采用瓦斯爐煎藥,要在一旁守著。”
中藥店戰火中幸存
劉家祖籍中國廣東梅州大埔,第一代來到南洋的劉鎮江一手創立葆和堂,接手的第二代繼承人劉萍及第三代劉聿明也同為中醫師,以家傳醫術造福居鑾民眾。現年七十余歲的劉聿明至今還在葆和堂內看診,他根據先父劉萍所述,講述了葆和堂如何在戰火中僥幸留存。
在1940年,家中長輩購入葆和堂,裝修好內部家具和采購貨物,開始經營中藥店,當時店內排滿了各類中藥材和酒類。“1942年,居鑾繼峇株巴轄和亞依淡之后淪陷,大批日軍入城。那一年,我只有4歲,父親決定暫時放棄在毛申律大街剛買下不久的三層樓店屋,舉家搬遷到市郊花旗山(豆沙村)的森林邊沿安頓。”
劉聿明憶述,進駐居鑾的日軍霸占當時的葆和堂充做憲兵司令部,隔鄰的25號店屋則被充作日軍慰安所。為了方便軍官前往慰安所,日軍更在2間店屋二樓之間的墻壁敲開一個大洞。3年8個月后日軍投降,他們一家重返葆和堂,只見店內貨物已被洗劫一空,欲哭無淚,只好再次到新加坡辦貨。
“所幸當時主要的櫥柜和設備沒有遭受嚴重破壞,包括樓下兩邊墻上的貨物木架和店內現今仍在使用著的木質長柜臺,否則先父真的不知該如何重置家業。”據了解,店內古色古香的百子柜已有近百年歷史,是開業之時自新加坡帶回的柚木家具,全以榫頭連接,不含鐵釘。(張柔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