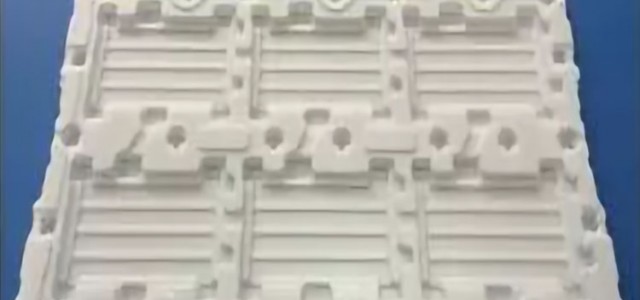攝影記者 | 蔡小川
“女士們先生們,列車已經到達武漢站,請您按照先后順序下車……”
廣播響起來的時候,車廂里的氣氛陡然升到了最高點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車窗外夜幕之下黑壓壓的城市。一個列車員從車廂一頭飛奔過來。“前面有兩個人要在這里下車,還有誰要下?”我看向她,還沒開口,她就明白了:“你是不是也要下?你怎么不早說?身份證拿來!”這下,全車廂嘩然一片,全都看向了我。有人在議論:居然有人在這兒下車!
這是1月27日晚上,武漢封城后的第五天,我在G69列車上。
2020年1月27日武漢站
前一天,圖片總監宋文發信息問我:你愿意去武漢嗎?我秒回:可以。我所在的《三聯生活周刊》社會部的同事早就奔赴了現場。對于我而言,這個年,父母見過了,爺爺奶奶姥爺姥姥的墳也去拜了,基本上算是了無牽掛。我本來準備和爹媽做做思想工作,出乎意料,他們很快就答應了,只是說讓我做好防護。這估計和我常年出差不著家有關,他們早就習慣了。
如何進入已經封城的武漢?記者王珊指了個方向,買從北京到廣州的一趟路過武漢的火車,會在武漢經停。“你就那時候下車。”電話掛斷前,王珊叮囑我多帶點口罩,她說他們手上只有一次性醫用口罩。
帶著老媽給的幾個口罩和圖片總監宋文交給我3身防護服、3個醫用口罩和3個護目鏡,我坐上了去武漢的火車。火車人真不少,每個人都裹得嚴嚴實實。周圍不斷有人咳嗽,氣氛顯得非常凝重。也有心大的一家脫了口罩就喂孩子吃橘子,看得我目瞪口呆。為了松口氣,我給好友發消息:我去武漢了。他們不知道說啥,只回倆字:“保重。”
我拖著行李站在車門前等著開門,10秒,15秒,門像撒氣了一樣開了。目測這趟列車有十來個人下車。下車的人都不說話,低著頭朝出口走去。還有人想上車。出站口,一個男人拼命往站里沖,被工作人員團團抱住。他攥著手機,屏幕亮著,上面顯示了兩個字“武漢”。
武漢站出口遠處的顯示牌上寫著G69到達武漢的時間
武漢整個交通系統全部停運了,同事潘鴻和文字記者張從志幫我聯系了兩輛車。一位志愿者開車載上我,送我去和另一位好心市民匯合。她自愿把自己的私家車提供給周刊使用。這位姐姐見到我,先打開后備箱交給我2瓶酒精,讓我及時消毒,這可是武漢的稀缺物資。她說,后備箱沒時間收拾,都是些空酒瓶,讓我湊合著開。我就拖著這些叮叮當當的酒瓶朝記者奔去。
見到記者就像親人團聚。在這天結束以前,我們先要送一家醫院的采訪對象回家,他不會開車,限行之后出門都成了問題。他們在車里聊著武漢現狀,我開著車正好經過武漢長江大橋。八車道空空蕩蕩,大家唏噓不已。到賓館的時候,記者和我說他們今天采訪的一個醫生確認了肺部感染,我們相視無言。
封城后的武漢二七長江大橋
以下就是我用鏡頭記錄的武漢。
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位于武昌區東湖路169號,是一家三級醫院。這是我拍攝的第一家醫院。
急救車剛送進來的重病號
在來之前,我不清楚自己作為一個圖片攝影能起到什么作用,我來拍這些東西是想說明什么,但我想如果不能在這個時刻近距離記錄他們,可能也是一種冷漠吧。
忙碌的醫護人員
剛到這里時,我抓緊戴上了口罩。門診就有一個搶救室,里面有病人在搶救。
老爺爺在門口看著搶救的老伴
我在門口等了很久,病人終于出來了,插著呼吸管,被醫務人員推去病房。我覺得她可憐,又覺得她幸運,畢竟相對于外面等待病床的患者,她起碼已經得到了救治,生存上有了一線的希望。
戴著不合格口罩的家屬,在疫情面前一樣陪伴在家人身邊。我看著揪心,也許,在這個時候親情能讓人忘掉病毒帶給人的恐懼。
我在搶救室拍了很久,最終不得不出去透了一口氣,這種環境太讓人窒息了。
相片還是能記錄下一種文字無法描述的氣氛,老爺爺的大手,老派的眼鏡,花白的頭發,他們在交談什么,我們雖然聽不到,但那種焦慮彌漫在空氣里,誰都能感受到。
在醫院里,語言仿佛失去了作用,醫務人員、家屬大家都在訴說彼此的難處,誰都沒有解決的辦法,醫院沒有多余的病床,病人依然住不了院。
醫院外面,一位女士咳嗽到不行,又住不進病房。我看到了兩個人的絕望,想要拍出來,卻不知道怎么去表達,只拍到了兩個人的沉默。
武漢的立交指引著汽車前行的道路,卻不見過馬路的行人和車輛。
空曠的戶部巷天橋下
藍色的線條指向道路遠方
零星的樹葉,空曠的街道
出行只能靠蹬車了
記者張從志在武漢上了4年大學,他告訴我這條路是楚河漢街附近非常有人氣的街道。
老人還是習慣在出太陽的時候出來晾衣服。
拍這張只為左下角那位抱著琴的老人,琴聲帶給整條街一絲生氣。
在清晨的霧氣中,我們朝醫院行駛。
這里哪里像2020年的武漢。
武漢市第七醫院是武漢當地一家二級醫院,是武漢市第一批定點醫院。這個醫院設施一般,看起來有點像我以前采訪拍過的鄉鎮醫院。
大量的氧氣瓶被送進醫院
陰冷的武漢終于出了太陽,讓醫院顯得沒那么冰冷。
我進去之前,就看到醫院門口各個顯著位置都貼著“床位已滿”的公告。走進門去,右手邊是一個輸液房間,一排排座位上是一排排輸液的人,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么多人一起輸液,這個場景讓我覺得心里很震動。
七院里聚集了不少來打吊針的人
我用語言描述不出來,大家可以看看照片。為了避免感染,這些患者多是自己一個人過來,我看到許多年紀很大的老人,顫顫巍巍,也不知道他們是怎么在封城的情況下來到醫院的。
來醫院的患者,選擇雨衣作為防護工具
住院患者和家屬
醫護人員穿上了防護服,大家互相認不出來,就在衣服上寫上了部門和自己的名字。
CT室的工作人員說,現在是來一個人拍一個,根本沒有上下班之說。
1月30號我們拿到了18個N95口罩,心里有點高興。后來記者王珊去采訪時,得知醫院口罩急缺,一個口罩要用4天,她給我發消息讓我把那些口罩全部拿給醫院。我并沒有同意,好不容易有了些N95,最好還是自己先留著,據說第二天還會有100個KN95口罩能給我們。我說這18個我們就留下吧,明天給那些,王珊怒斥讓我別廢話。她捧著這些N95口罩給醫生,對方拿到手里看了下,說這是防霧霾的口罩,醫院用不了。又是一通沉默。
和第七醫院一墻之隔的居民樓,左邊的老奶奶在曬著太陽織毛衣,右邊的老爺爺和老奶奶在晾衣服,這樣的場面讓人抱有對美好生活的希望。
高樓上的霓虹燈寫著武漢加油,大家都宅在家里,這又是給誰看呢?
出來就是一天,兩位記者在后座睡了,我朝著賓館開著。